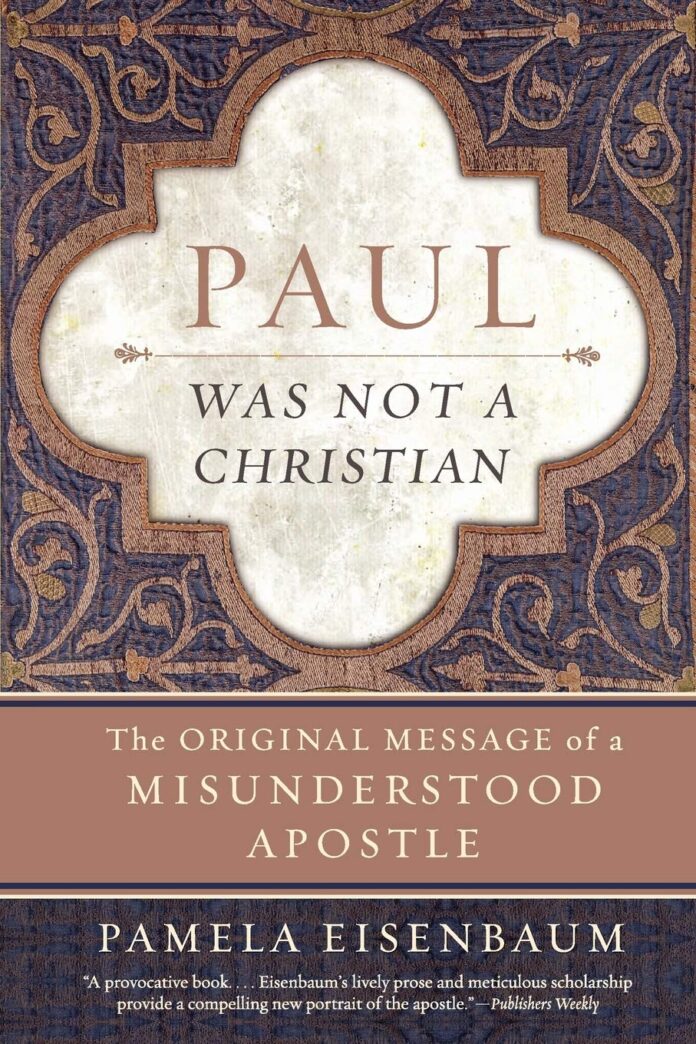- 四角賽(1):保羅神學的話語權
- 四角賽(2):傳統保羅:「我是基督徒,不再是猶太人! 」
- 四角賽(3):大戰前夕––– 「新觀保羅」,傳統派的「敵人」來了!
- 四角賽 (4):「傳統」大戰「新觀」的死局
- 四角賽 (5):突破死局,尋求出路
- 四角賽 (6):可以不再用人的系統去貶低聖經的基督嗎?
- 四角賽 (7):超理智的福音派,應該跟「天啟派」學下野…
- 四角賽 (8):瞄準基督教「開火」的新興保羅神學:「極端派」(Radical Paul)
- 四角賽後話
當「天啟派」的保羅以為自己已經「升到天上」,「極端派」 的保羅卻堅持「留在猶太人的地土上」。「極端派」又名「在猶太教裡的保羅」(Paul-within-Judaism),反對「傳統派」及「新觀派」視保羅為反猶太教,或視教會為取替聖經裡以色列的身份。1 他們高舉保羅的猶太背景,認為所有其他的派別,都犯了時代錯置的錯誤,以後世的基督教的思想讀入第一世紀的保羅 (anachronistic Christianization)。2 在他們眼中,上主給保羅的召命,是叫他成為「非猶太人的使徒」(an apostle to non-Jews)。3 保羅寫的信,全都是為了基督的外邦跟隨者而寫的,故此我們不應將他對外邦人的處境性勸勉,系統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甚或看之為針對猶太教。4 保羅從未要求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保羅以及其他猶太人 (Judaeans),在跟隨基督之後,仍然維持他們猶太教徒的身份,並繼續持守摩西律法各樣的要求。5 簡單來說,保羅根本不是一個基督徒!6 極端保羅會這樣說:「我是猶太人,我不是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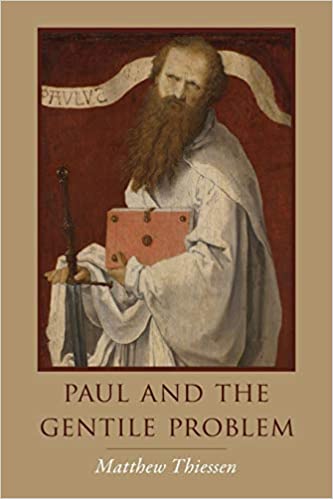
「極端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有納諾斯 (Mark Nanos),塞特霍爾姆 (Magnus Zetterholm) 及蒂森 (Matthew Thiessen) 等等。7 「極端派」的學者認為,第一世紀的宗教世界,都是以人類種族的族譜概念 (ethnic genealogical lines) 去建構的。 8 換言之,神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透過血脈的連結而成。今天我們所謂的「皈依」(conversion),在第一世紀,其實是透過加入別的神人血脈家庭去成就的。9 憑信接受基督只是為外邦人而設, 10 他們亦因著領受聖靈,得以歸入上主給亞伯拉罕的應許。1112 按這樣的理解,跟隨基督的「始源」,就完全是出於以色列或猶太教。 保羅處理的問題,不是猶太教與基督教兩個宗教之間的關係,而是外邦與猶太社群,如何能帶著不同的律例守則,共存一教(intra-ecclesial)之內 。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的會議,是一個猶太人內部會議 (in-house Jewish debates),其目的就是討論如何讓外邦人只須遵守部份猶太教的規條,但又能把他們「吸入」猶太人的「大家庭」。 13
值得留意的是,保羅雖然要求外邦信徒遵守猶太教的個別規條,但他卻反對外邦人接受割禮,因為割禮不能叫外邦人超越上主創造的「家譜間隙」 (“the genealogical gap”),以致能成為亞伯拉罕的子孫(這是人的方法)。14 上主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讓聖靈內住外邦人的內心。15 故此,保羅反對外邦人守割禮的原因,不是為了打破這「間隙」,以致能建立起一個猶太人及外邦人以外的「第三族群」(a third race)。16 相反,保羅繼續沿用這個以種族族譜為本的宗教概念,確認它的有效性,並且視聖靈的內住,作為外邦人已被上主接納為亞伯拉罕家族 (Abraham’s lineage) 的明證。17 神的恩典,就是這樣跟人類的家族概念,疊在一起 (God’s grace and human lineage coinciding)。18 如此,「極端派」聲稱已成功重尋歷史中的保羅。保羅當時的聽眾其實能正確掌握他的意思的,但後來的信徒,卻全都誤解了。19 這樣,「極端派」對歷世歷代基督教發展的合法性,作出猛然的批判。在他們眼中,往後的教會徹底地錯解了保羅及猶太教。上世紀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種族滅絕行動的源頭,其實就與基督教錯解保羅有關。20 基督只是為外邦人而設,猶太人基本上可憑律法得救。所謂基督徒,其實是一班靠著基督,歸入亞伯拉罕應許 (Abrahamic promise) 的外邦人。

至此,筆者要對「極端派」作出批判。當「新觀派」漸漸定位自己為「傳統派」的更正版或補充篇,「極端派」卻定意要徹底否定整個教會的發展,將猶太化推往極致。教會過往有否誤解,醜化甚至否定猶太人在上主國度裡的角色?我認為是有的。但諷刺的是,「極端派」藉著否定保羅的基督徒身份,似乎要「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我不是說他們要報仇,但以所謂「歷史新發現」去包裝自己的詮釋框架,然後套入《聖經》的文本,其實不是什麼新事。然而,他們之所以配稱「極端」這標籤,是因他們漠視保羅定意以基督為根基,去建立一個新身分 (new identity)。21 蒂森以「族群論據」(ethnic reasoning) 去總括保羅的神學邏輯,正是為了高舉保羅的猶太人族群身分,並否定他的基督徒身份。22 在蒂森眼中,這以基督為首的身分,是一種不符歷史既有族群的「擬親屬關係」(fictive kinship),所是應該是不存在的。23
然而,根據保羅的手筆,我們清楚看見基督是那結連猶太人及外邦人的唯一根基(房角石);24 猶太人與外邦人都是因著同一位基督,藉著同一位聖靈,得見同一位父神;25 無論猶太人或是外邦人,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26 因為「惟獨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27 至此,我們或許能明白,為什麼蒂森必須假設保羅的書信,都只是為外邦人而寫了。唯有保羅書信變得與猶太人無關,書信論及那以基督為本的新身分,就自然不適用於猶太人身上了。如此,蒂森及「極端派」,理順了他們以歷史蓋過保羅見證的邏輯,將自己與保羅無可推諉的見證絕緣。

誠然,保羅並未否定基督徒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28 但在這重疊的關係上,保羅顯然選擇了以基督,去界定這個新社群身份。29 若基督只是一條外邦人歸入以色列的橋樑,保羅就應該說亞伯拉罕是房角石,30 我們是藉基督歸入亞伯拉罕了!但保羅沒有這樣做。在保羅眼中,上帝的義,已經在律法之外顯明出來。31 無論是猶太人抑或外邦人,都需要在基督耶稣裡的救贖。32 否則,彼得就不用在五旬節向猶太人傳講耶穌,勸他們悔改了。33 上帝在基督裡的工作,雖然是成就了祂對亞伯拉罕之約,但在祂裡面的新生命,卻是本質上的新創造 (new creation)。34 回到筆者於本文起首的錦標賽比喻,或者最能痛擊「極端派」球隊這種以過去遮蓋基督新創造的戰術,正是「天啟派」球隊只講新創造,忽略上帝過去地上工作的戰略吧。35
大家好,我是葉應霖。英文名是 Scott。希望您藉著呢個網更深認識神,別人及自己。
Footnotes:
- Magnus Zetterholm, Approaches to Paul: A Student’s Guide to Recent Scholarship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127, 61; Matthew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
- Mark D. Nanos, Paul Within Judaism: Restoring the First-Century Context to the Apostle, ed. Magnus Zetterhol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5), 4–5.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0–1.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4; Paula Fredriksen, “How Later Contexts Affect Pauline Content, or: Retrospect is the Mother of Anachronism,” in Jews and Christian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How to Write their History, ed. Peter J. Tomson and Joshua J. Schwartz (Leiden: Brill, 2014), 35. 「極端派」會以耶穌「跟隨著」(Christ-followers) 的表達,去取代耶穌「信徒」(Christ-believers)。
- Fredriksen, “How Later Contexts Affect Pauline Content,” 36; Paula Fredriksen, “Why Should a “Law-Free” Mission Mean a “Law-Free” Apostle?,” JBL 134 no. 3 (2015): 638;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8–11. 根據蒂森對林前七19的理解,守割禮(猶太人)或不守割禮(外邦人)都是沒有問題的。猶太人及外邦人都不須改變自己的宗教模式。繼續遵守上主給他們個別的誡命,就可以了。
- Pamela Eisenbaum, Paul Was Not a Christian: The Original Message of a Misunderstood Apostle (New York: Harper One, 2009), 3–4.
- 值得留意的是,「極端派」的學者,不一定是「基督徒」。另一方面,他們的意識形態,亦跟政治運動「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非常相似。參 Du Toit, P.La.G., 2017, ‘The Radical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Messianic Judaism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Christian Zionism’, HTS Teologiese Studies/Theological Studies 73(3), 4603. https://doi.org/10.4102/hts.v73i3.4603
- Fredriksen, ““Law-Free” Mission,” 639–40. 參加一14:「祖宗的遺傳」。
- Fredriksen, ““Law-Free” Mission,” 646;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3.
- John G. Gager, Reinventing Paul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6, 25.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59–60.
- Mark D. Nanos, The Mystery of Romans: The Jewish Context of Paul’s Letter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96), 32.
- Fredriksen, ““Law-Free” Mission,” 639;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2–3; Bird, An Anomalous Jew, 23–4. 聖經學者迪圖瓦反對「極端派」對徒十五的看法。他認為那一次耶路撒冷會議的性質,更像猶太信徒與外邦信徒之間的妥協和解會議。根據使徒行傳的脈絡,筆者也贊同迪圖瓦的觀點。詳參 Du Toit, ‘The Radical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4–6.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2.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3.
- Magnus Zetterholm, ““Will the Real Gentile-Christian Please Stand Up!” Torah and the Crisi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Conflicts, Contacts, and Construc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Bengt Holmberg, ed. Magnus Zetterholm and Samuel Byrskog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12), 374.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3. 蒂森: “God had rewritten gentile genealogies in order to bring them into Abraham’s lineage.”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2.
- Gager, Reinventing Paul, 150.
- Bird, An Anomalous Jew, 8. 納稅德軍於二次大戰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以及1948年以色列的復國,的確整體地改寫了西方社會對猶太人的觀感。這或多或少也造就了「新觀派」及「極端派」的冒起。
- 弗二15:「廢掉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使兩方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促成了和平」。
- 參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3.
- Thiessen, Paul and the Gentile Problem, 163.
- 弗二20:「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 弗二18:「因為我們雙方藉著他,在同一位聖靈里得以進到父面前」。
- 加三27:「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
- 西三11:「在這事上並不分希臘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未開化的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獨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 加三28:「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
- 林前十二13:「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並且共享這位聖靈」。
- 弗二20:「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 羅三21:「但如今,上帝的義在律法之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 羅三24:「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藉著在基督耶穌里的救贖,就白白地得稱為義」。
- 徒二14, 37–8, 五31。另參羅一16; 十1; 十一26-32。
- 林後五17,羅六4,羅六15。基督與上帝過往在以色列人裡的工作之間的連繫性,屬另一研究題目,在此不能詳談。簡單來說,既有「連續性」(continuity),亦有「斷裂性」(discontinuity)。從身分認同 (identity formation) 的角度,「傳統派」及「天啟派」都過分側重後者,以致忽略上帝若干在猶太人當中的工作;相反地,「極端派」就過分強調前者,將基督的影響範圍縮窄為外邦人。「新觀派」就兩者兼具,但身份來源始終為後者。就此,「新觀派」是較為可取的。
- 縱使「天啟派」與「極端派」各走極端,前者整體的神學仍然屬於正統更正教之內;後者則已嚴重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