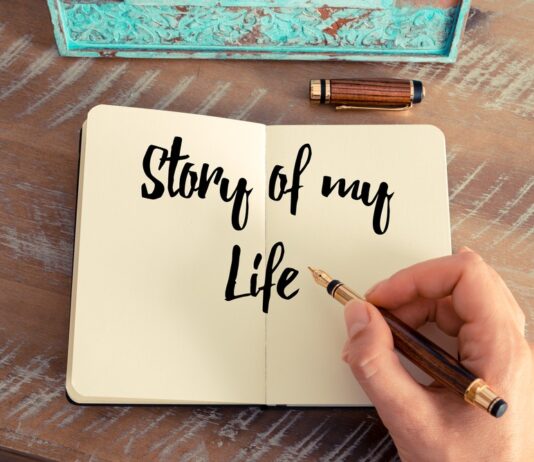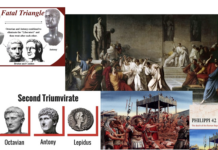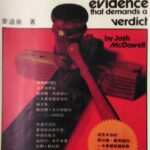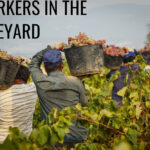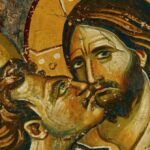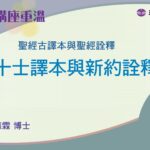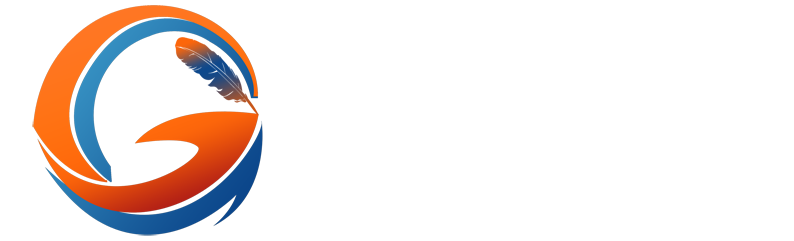沒有客觀證據就不能有確據?
三十年前,我信了耶穌。那時,我常常閱讀一些護教學的書,例如《鐵證待判》, 《你為何要信》 。初信的我,特別喜歡尋找一些客觀存在的證據,讓我知道這個信仰,是有根有據,而非一個主觀感覺而已。當我讀到聖經原來有那麼多的歷史客觀證據,幾千個應驗了的預言,千萬種考古學的引證時,我實在感到萬般的興奮:我找到了!《聖經》是真的!因為我在《聖經》背後的世界,找到客觀的事實。所以《聖經》是對的,值得我相信。雖然我知我所信是超越科學,但最能支持我相信的,卻仍然是一個建基科學的知識模式 (epistemological model)。雖然我穩定出席聚會,積極事奉,甚至參加門徒訓練,學習向人傳福音。但在我的腦海裡,仍然時不時有一把聲音在盤旋:「究竟我的信仰是否都是心理作用,不建基理性的主觀感覺?」更糟的是,若我們遇見一些反對基督信仰,質疑神的存在能否被證實的書時 (e.g. Why There Is No God: Simple Responses to 20 Common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我們的信心就會容易被動搖。回到教會,亦似乎不容易跟人分享這些掙扎…除非你團契導師或傳道人的...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我們每天都在講故事。每一天,我們都不斷聆聽,代入,創建故事去到認識神,別人及自己。每個故事都包含記憶,但記憶不僅是客觀機械式的數據存取,更是一份主觀投入的印象。記憶,本來就是一份不斷演變的故事。藉著記憶,我們找著我們的身份,不斷探索「我是誰」。詩篇22篇裡的主人翁,正正就是在回憶裡講故事,在故事裡尋索上帝及自己...
利科思想對詮釋馬太福音二十章1~16節「在葡萄園做工的比喻」的貢獻
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是一位法國哲學家,在二次大戰期間成為戰俘的經歷是他擴展學術視野的重要契機。他「集百家之大成」結合詮釋學、現象學、文學、哲學、符號學等多門學問的菁華,再進行化解與提煉。利科亦發表過不少有關聖經詮釋的文章,其詮釋理論對於聖經詮釋有莫大的貢獻。
猶大是否被上帝預定去出賣耶穌?
預定論 (predestination) 的確是基督教神學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意思大概是,上帝在創世之前就已經揀選了那些人將得救,甚至是那些人不會得救 (double predestination)。這樣,出賣耶穌的猶大或許就是其中之一。若是這樣,猶大就不單是一個「悲劇人物」 (tragic figure),甚至是上帝救恩計劃的「受害者」(victim)。這種救恩,我還應相信嗎?
其實這教義在聖經中也的確有一些基礎,主要來自於《新約》的一些經文。例如:
1. 以弗所書 1:4-5:
洪水泛濫之際,反思世界現況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創世紀六章記載的洪水之所以來臨,是因為當時的世界生態已經變得不宜居住。之所謂生態,不單是指自然生態,更是指當時人的道德及屬靈生態,已經壞到一個極度惡劣,甚至可以用邪惡去形容的程度。當大地受盡人的摧殘,洪水正是人種之因所得的果...
剖釋利科思想對聖經詮釋的貢獻—— 以兇惡園戶的比喻作為例子
作者:羅樂呈
1. 引言
利科採取的哲學詮釋學,以符號、象徵、隱喻和文本來理解人的存在與意義,提出「三重模仿理論」結連敍事與生活。 相較於傳統的釋經手法,例如從經文細節觀察作歸納式研經或歸納命題式教義,利科的敍事詮釋更能幫助讀者落實「基督的模仿者」的步驟。本文將以耶穌的兇惡園戶比喻(太二十一33-46)作例子,剖釋利科的各種敍事詮釋理論,與傳統釋經不同地對聖經詮釋作出貢獻。
2. 經文背景
兇惡園戶的比喻出現於耶穌在受難週進耶路撒冷城後,在聖殿教訓人的時候被祭司長和長老質疑權柄(太二十一23-27)後,以三個比喻一併回應﹕兩個兒子的比喻(太二十一28-32)、兇惡園戶的比喻(太二十一33-46)和婚筵的比喻(太二十二1-14)。兇惡園戶的比喻同被記載於另外兩卷福音書(可十二1-12、路二十9-19),同是耶穌的權柄被質疑後作回應,唯只有馬太福音的記載是將三個比喻放在一處,是當耶穌對於猶太領袖指出神真正子民的問題時,以三個比喻來回應以加強效果,且作為耶穌在第二十四章預言聖殿被毀的重要鋪陳。
敘事覺醒 (3):怎懷舊事,怎添新意
真理的舞台若只是一堆概念,讀《聖經》應該很簡單,因為概念理應融會貫通,天衣無縫,放諸四海皆準。站到很遠的位置去望向《聖經》,自然就看見跨時代跨地域的《新約》基督觀、教會觀等。這種命題式的完美教義,有什麼新事可言?跟我們的困境,有什麼共鳴可言呢?
你的耶穌,不是我的耶穌?
在第一世紀初,一小撮猶太人先後拒絕了羅馬人,以及以色列宗教領袖以至群眾的十架故事。在神的引導下,他們選擇了主耶穌的十架故事。然而,救恩的成就卻不是故事的結束。相反,教會的誕生代表敘事角力已進入新階段。以猶太人為首的初期教會,隨即面對一個新的敘事難題:以色列的復國故事,究竟應該怎樣與主耶穌死後升天的故事連結呢?當知道,所有使徒都是浸淫在地上重建以色列國之傳統下成長的。如今,他們必須重新回望與重述 (retrospectively re-narrate) 舊約各段經文的意義。可以想像,這種故事的重寫,殊非容易,甚至是極度困難。處理得不好,教會未成立就可以已經四分五裂。試想,每位使徒都是一位「性格巨星」。他們又已「拿正牌」,有足夠權威去自立門戶,豎立他們自己理解的「耶穌教」,制定他們的「政教關係」,定準舊約經文的新意義。神帶領的合一教會,怎麼可能?
1. 不只是一般的「行事為人」
很多人喜歡用羅馬書十三章去理解保羅的政治神學,我更喜歡用腓立比書。然而,腓立比書的信息不就是喜樂,彼此謙卑服侍嗎?抱歉,我認為這理解有點膚淺。究竟保羅在腓立比書講什麼?要解開這個謎,我們一定要正確理解腓一27的一個動詞: πολιτεύομαι。為什麼?因為根據希臘修辭理論 (Ancient Greek Rhetorics),腓立比書的中心思想,可以在腓一27–30節這段落裡找到。細心閱讀原文,就發現一27–30這四節,原來同屬一個句子,而 πολιτεύομαι 就是整句的唯一主要動詞 (main verb)。故此,πολιτεύομαι 在腓立比書的角色,可說是重中之重。你如何詮釋 πολιτεύομαι 的意思,就會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你對整卷書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