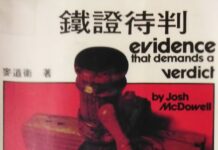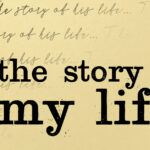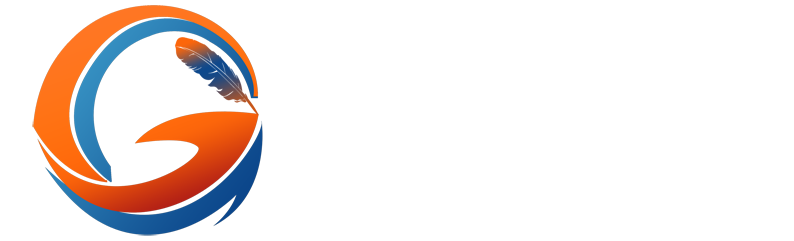不羈小野馬,安頓在主裡:當 ENTP 遇上 7號
作者:YY
引言
修讀「性格與靈命成長」課程,帶給我許多驚喜與啟發。它不僅幫助我掌握MBTI與九型人格的理論與應用,更引領我探索敘事神學與耶穌比喻的豐富內涵,開拓了我對信仰的新視野。在撰寫這份反思文章的過程中,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在靈命旅程中的盲點與偏執,也嘗試將課程所學與對性格的認識整合起來,進一步反思上帝如何塑造我的靈命與品格,引導我走向更成熟、更健康的生命方向。
生命回顧
我出生於一個大家庭,我有很多位姊姊及幾位弟弟妹妹的。父母並無特別的生育計劃,母親因不想被奶奶嫌棄和鄰居取笑,才努力追求生下兒子。父親沉迷賭博,經常無法提供家用,甚至在我出生前曾考慮將我賣到荷蘭以換取生活費,所幸最終因不捨而放棄。從小,我目睹母親肩負起撫育兒女和賺錢養家的重擔,對她充滿尊敬與憐憫,並仿效了她自強不息的精神。然而,童年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缺乏關愛、物質供應和監管,我幾乎是在「放養」和「自生自滅」的環境中成長。若沒有認識主耶穌,我難以想像這匹不羈的小野馬會奔向何方。這段經歷也讓我對被嫌棄或拒絕的恐懼深植心中,影響了我的人生軌跡。
人生牌局:INFP 與7號仔的靈性探索
作者:羅樂呈
引言
以往我會形容自己的性格為「樂天」、「堅強」,理解性格為待人處事的客觀特徵,跟個人內在的靈命成長互不相干。經過課程中一系列對性格理論的學習,糾正了以往跟從坊間的性格分析工具,不再以行為特徵歸納和定型自己的性格,而是從意識層走進自己的潛意識層,發現自己一些自己以往都沒留意的自然反應和傾向,發掘這一出生已內置、一直主導著自己的性格劇本﹕INFP七號仔。
發掘自己性格是一個發現自我意識中的不完整、不協調和偏差的過程,靈命成長需要對自己的性格常存一種「健康的懷疑」來幫助自己不斷重新評估對自我的認知。 性格影響著我如何自我界定,也是我認知屬靈經驗的輪廓,影響著我與人、與神交往的風格。固然在教會中每人都是按著同一本聖經受教導,參與在同一樣的崇拜模式,每人卻有著與神交往的不同風格和屬靈特質。按著課程學習到的性格理論,這對靈命成長的幫助始於認識到自己類型的生命盲點和與神交往的偏執(人生如牌局中,一開局手上拿著的「手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聖經的宏大敍事超越自己原先無意識地讓性格主導自己的敍事(如何打出「手牌」,打出精彩的人生牌局),形成獨一無二、個人化的靈命成長藍圖。
上帝給我的「手牌」
重述記憶中的我:敘事神學的信仰反思
因著認識敘事神學,隨之而來明白對於認識故事投射的世界觀並讀者是否願意全程投入故事世界之中,容讓故事與自己的舊有故事「相撞」、更新與重塑存在著一個持續並動態的挑戰,正因如此使信仰能夠更立體地與人的生命結合、更新並重新詮釋。
在《幻愛》裡尋「真實」
《幻愛》是一套超越眼前現實及社會界線的電影。作為一套觸及潛意識的創作,它不單充滿夢幻與愛情,還有濃厚的「榮格治療」(Jungian Therapy) 色彩。我十分欣賞電影著重愛,過於精神病態的角度,去描繪主角的歷程。戲裡叫男女主角得救贖的方式,不是藥物,而是一種不離不棄的接納。
INTP x 3W2 「最強的人不是自己有多強,而是帶動團隊成為最強。」——由獨行者到利他者的蛻變故事
「我不喜歡被困鎖,我更喜歡跳出枷鎖,自由自在地翱翔天際。」
「我不會輸,我只是未贏。」
「你認為我甚麼都懂,因為我從不展露我不懂的時候。」
「我很寬宏大量,氣度不凡,但請不要得罪我,因我不懂得原諒你。」
「我是最有魅力的,如果你不接納我,我會自行尋找我的舞台。」
「我未必懂得尊重你,但我渴望得到你的尊重。」
「請看見我,請不要忘記我,請接納我,請愛我。」
我是誰?
在不安中尋求忠誠的敘事角力 —— INFP+6號
1. 引言
筆者從前對MBTI和九型人格的認識不多,只嘗試做一些坊間的測驗,只停留在認識自己屬於甚麼類型的階段。因為認識自己不深,所以每次做這些測驗都會覺得疑惑,總覺得自己不似測試結果的類型,而是似另一類型的性格。經過這個課程和這次省察的旅程,卻讓筆者發現真正的自己,並且透過MBTI和九型人格這些工具,讓筆者重新認識以往的人生經歷怎樣塑造自己的性格特性,而且亦可以嘗試為以往的測試結果檢證一下。
...
ISFP x 4:無止境追尋自我,抬頭卻是祢叫我停下
透過學習MBTI的理論,我看待自己和別人的角度都變得豐富,更能發掘人的美善,同時又解開了一些我對於自己的標籤,使我能對自己溫柔一點,也多一點欣賞。至於九型,在自我反省的過程中揭示了我的核心恐懼如何扭曲了我的自我形象、造成的偏執,無人能夠避免被罪所苦,唯有上主的恩典和拯救才能帶給人盼望。我嘗試拆解偏執的運作機制,雖不可一蹴而就解決,但拆穿虛幻的面具以致我能邁向活出上主所造那個真實的我的路徑。
ENTP x 8:究竟我是一隻凶狠孤狼還是可親哈士奇?
我是一個青少年工作者,無論職場還是事奉,我都是從事與青少年有關的工作。所以「成長」這個課題是我每天需要面對的事,可能是觀察青少年人的成長、指引他們成長、理解他們為何不願成長等等。MBTI與Enneagram有時也是我嘗試去了解他們的工具,我會在一些有關成長課堂向他們提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說法,意指若要成長,必先清楚自己的為人,也要理解身邊其他人的性情,才能好好地處理不同的關係。會有如此以上的說法,是因為自己在成長階段太遲察覺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導致很多不能逆轉的事情發生了。這次課程,我終於要好好面對自己的性情和成長。